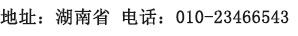白癜风诊疗目标 http://news.39.net/bjzkhbzy/171011/5751913.html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是在满天云霞下面,失魂落魄地跑着。西山上的太阳明煌煌地,像那个人的灵魂一样燃烧着。灰暗的落日如一颗头颅般从红色的天空上缓慢地跌落下来。遥遥望去,那些被冻僵的白雁飞得极低,快要触到草原的地平线了。暴风雨要来了。快躲!她那颗软而小的心脏随着奔跑剧烈地颤抖着。积雨云从东南西北压来,犹如大团的泼墨洇向纸上的一只困蚁。还是迟了一步。随着一声巨响,大雨瓢泼,尘土飞扬,空气里灌满了浓重的土腥味。沸腾的铁水向她兜头兜脸地浇下。她一头扑进了树荫下。喘息咳嗽片刻后,她开始龇牙咧嘴、哎哟哎哟地把自己的长筒袜腿上撕下来,它们已经被血水黏得很结实了。之后是衬裙、手套,全部。她翻了个身,看着自己锈迹斑斑的身躯。“真倒霉,今天都走不了路了……”这是一棵魔法般的密不透风的巨树。她抬头向上看,大雨仍在头顶隆隆作响,发出嘶哑的恫吓。浩荡浊流在树外的世界里瀑天瀑地地滚沸在一起,不辨东西南北。那被暴雨烫伤的躯体仍然在止不住地发抖。“风铃呀,雏菊呀,蓝色的补血草呀。”她这样轻轻地嘟哝着没用的小咒语,俯身往自己溃烂的左腿唾了些嚼烂的碎草片。这是一个浑身淡蓝色的年轻女孩子——连血管也是幽幽的蓝色。远处的暴雨中,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向她一点一点移动过来。“谁啊?谁在那边?”她警觉起来,一骨碌爬起来披上衣裳,大声地问。若是躲雨的人还罢了,如果是那些讨厌的蝴蝶精怪和槲叶老头……离得近些,她才发现白的是跳动的雨珠和水雾。那人开口了:“请问这是你的金合欢树吗?是的话,能不能……”“不是!但是你也不要靠近我!”女孩大喊道。轰隆隆!一道紫白色的闪电突然劈下来,这一瞬间好像整个天地都被照亮了。女孩看清了这是个戴着兜帽的穿着红衣服的男孩。不仅是衣服,整个人都是一种怪物般的淡淡红色哩,双手,脸颊,耳朵尖……女孩暗暗地想。被她这么恶狠狠地一吼,男孩怔住了。而且,他显然也发现了她的模样和自己完全不同,有些骇异地睁大了眼睛。“这……我有一项本事,我可以给你生火……”“那更不需要!”女孩一边冷漠地说,一边用手指着原野的那边,“你快走吧!”他听完果真尴尬地把手背到背后,稍微踮了两下脚,然后怪委屈地不声不响地走了。草地被大雨擂得泥浆飞溅。而他已经浑身湿透了。这是个很有礼貌的人。好像怪残忍、怪不近人情的……这样把他赶进那么大的雨里。女孩想。“等等!”她叫回他。“不是说能生火吗?把我的鞋袜弄干,就让你留下来。”其实,女孩是不需要特意弄干衣服的。之所以让他留下来,是出于无法言传、从未有过的一种心情。她和她的族人是在一次向北的迁徙中走失的。随着天气变暖,他们决定离开原先的居所,在极北的城市中建造一座玻璃大厅,然后世代永远居住下去。他们不习惯交谈,也互不登门拜访,总是披着长长的黑黑的斗篷,急匆匆地穿梭在暴雪和狂风中的冰原上。偶尔他们也在夏天出现。六月的清晨,人们看见白玫瑰上结了浓霜,就说明蓝血管的人们曾经造访于此;失去了未婚夫的裹着黑纱的少女,能够在水中看见他们蓝色的没有声息的倒影;月圆之夜,失眠的人在枕上听见山海呜啸,那是他们正成群结队地从远方走过。这样,蓝血管的孩子和红血管的孩子就相背着在一棵大树下面等待着大雨过去,谁也不说一句话。要不要开口呢……?彼此这么想着。要不要说些什么呢?最终,他们什么都没有说。雨在傍晚停了。月亮升起来了,像一朵蜜香的白栀子花,里面略微有些虫蛀的痕迹。河流在黑暗中暗暗地闪烁着,几条小鱼在里面发出拨剌的微响。天晴了。原野上的太阳是那么酷烈,亮得眼前一阵阵发黑。蓝血管的姑娘浑身布满淡蓝色的血锈,独自坐在碧青色的山坡上唉声叹气。“唉……”“越来越丑了,”她自言自语道,“不要见人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这样无聊地想着,一边不断用草叶擦掉蓝色的锈迹。眼前忽然一暗。不知什么时候,他站在了自己面前。“走。”她下意识地说,语气生硬得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尴尬地笑着:“我是帮你弄干鞋袜的。”这么说,是有这回事。昨天说的,一转眼就忘了。“要怎么……?”他带着点得意的神气,向她亮亮自己空空的双手。“瞧好了。”眨眼之间,他就凭空捞出一把细细的小刀,转手就往自己手臂上点了一下,快得她都不曾看清。“扑刺”一声,他的手臂上竟然迸出了流动的火焰。接着是一串红宝石一样的血珠子,嗵嗵哒哒地落在草地上。她吓得捂起眼睛;而他却哈哈大笑起来。那小小的伤口随之愈合了。他笑着走上前,掰开她的手指,向她展示了光洁如初的手臂。啊啊,这个人真是有点厉害……他看到她蓝灰色的眼睛闪亮亮的,有些不好意思。这就算认识了吧。他们一起爬上青郁郁的小丘,趟过珍珠般的溪流。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正如一切童话中的那样。他们见过一些被雨水泡涨了的鹅卵石上咕噜噜地冒出绿色的花簇,也见过金色的风沙中,像手掌那么大的荧蓝的蜻蜓密密麻麻地落在岩石上。有一次天空下起了比他们相识那天还大的暴雨,溪水中银色的飞鱼便腾跃而起,顺着雨流铺天盖地地从天空飞过去,粼粼巨浪无始无终,空气中的鱼腥气把他们都呛得咳嗽起来。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了寂静的地方。没有人讲话和交谈。许多的夜晚就这样地过去了,月光流着银色的血,绵密的草地上一片灰幽幽的微光,就像被困在魔法的海洋中一样。她不禁想,世界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都是这样地沉默着的。她和他相对无话地走着。有时候她的膝盖和手臂疼得受不了,便要求停下来休息。男孩总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但她往往稍停一会儿便会说:“可以了。”其实她的袖子下面、长筒袜下面,已经被锈斑硌得走不动路了。日复一日,霉斑和脓疮一样的深蓝色锈斑,正在不断地撕咬着她的血肉骨骼。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冰原,说不定哪一天,四肢百骸都会腐朽下去。其实是有点怕他嫌弃……她不吭声地想着。她还是那样的寡言少语。有一次,他们碰见过一个浑身戴着狼牙刺的男人。他的手中拿着一条长长的链子,那一头拴着一条无精打采的大蝴蝶,黄粉抖落了一地。“您向哪儿去?”男孩问他。“向哪儿去?我向哪儿去?”这一下显然把男人问住了。他不住地用布满刺针的手挠着同样布满钢针的脑袋,随后转向那只懒洋洋的蝴蝶。“向哪儿去?老兄,咱们向哪儿去?”蝴蝶吱吱吱地叫着,随后一下子把翅膀扇啦啦地抖开了。男孩和女孩面面相觑。一直到走远了,男人还在嘟哝着:“这下可把我难为死了……出发的时候,是想往哪儿走来着?”“你是要找那间玻璃大厅的吧?”等他走远了,男孩子问。“对。”女孩斩钉截铁地说。“我的家人都在那里。”这么一说,女孩忽然沉思起来:“那么,你又是哪里来的呢?”“我、我来的地方……”男孩突然间结巴了。随后他说:“你愿意听吗?这可是另一个故事了。”“我的家族一共有六十多个人,是一个很兴旺的大家族呢。我们世代居住在潮湿的低地,靠锻造和出售一些亮晶晶的小玩意儿谋生。那是一个和这里完全不同的地方,一年分为四季。春天的市集上,人们围在一起跳舞,女孩子们会制作姜饼小人送给喜欢的男孩子……春天虽说气候潮湿,但雨是沙沙沙地很轻柔地往下坠落的……”“下过雨之后是什么样的?”这一天他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女孩又困倦又疼痛,半躺在一棵巨大的开白花的树下。“唔,凉润润、昏沉沉的。风从我的身上冰凌凌地漫过去,贴着、吮着我的皮肤。人像在轻柔的水中一样。小水洼里漂着落叶和一些脏东西,蚯蚓在小路上横七竖八,褐色的树干被泡得黑黑的……”男孩一边说,一边看着眼皮打架的女孩。不知道怎么,觉得她像一块即将融化的春冰哩。“是真的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世界。”“真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他轻声又坚定地说。他慢慢地讲着,她在他难得静谧的声音中睡熟了。这是她第一次在他面前睡着。她有着松散的银蓝色的头发,略微凹陷的胸口,整个地像一个脆弱的梦。突然间,男孩看见她的手指开始染上了深蓝黑色的锈痕。接着是手臂。啊啊,怎么会这样……男孩睁大了眼睛。眼前的女孩就像是一座迅速坍塌的房屋一样,慢慢地皱缩在一起。骨骼、皮肉……整张脸腐烂得认也认不出了。女孩醒了。随着她睁开眼睛,她整个人也变得好转了一点,一些零零星星的蓝色的碎屑附在裙子的下摆。还有,眼睫毛上结了白色的霜。“怎么了?”女孩问。“刚刚有只天牛……”他局促不安地说。其实,是他有点喜欢上蓝血管的女孩了。然而,她却浑然不觉。她知道自己的身躯很快就会被异乡的气候毁坏掉。每一天,她都盘算着怎样不声不响地甩下他独自向北去。在他眼皮底下一点点烂掉的话……女孩打了个寒战。要想办法离开他才行。她要回到雪国去,在漠漠的风雪中修建起另一座玻璃大厅。冬日漫长,她将和血脉相似的人们终日沉默以对。——好像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红血管的人类一样。好像活泼的鲜血和年轻的眼睛是一种疾病一样。不能再等了。于是有一天,她生硬又突兀地说:“我想一个人走。”“啊?为什么?”“我想一个人走了。”她别扭地说着。“可、可是……”她分明听见那人火焰的血管哔剥地燃烧着。他的声音像遭了重病,而眼睛熄灭下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生病了。”她斩钉截铁地说,“一种会把你的火焰全部熄灭掉、让你的骨髓都结冰的病。没有人能承受那样的寒冷。”“是真的吗?但我不怕冷。”“是真的。”“那你自己呢?”她换了一副不耐烦的口气:“你怎么管那么多?说实在话,你可真是讨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怪腔怪调的不知好歹的人。”她一壁数落着,一壁用手推搡着他。“快走!不想再见到你了。永远不想见你了。”她的皮肤下面已经可以搓到坚硬的锈块了。他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草地上一溜火星,冒着一点烟气,很快就熄灭了。那是他的眼泪。唉,原来是真的喜欢我啊。黄昏的时候,她靠在一棵树下不断地想,不断地想着,心里哀伤起来。她一个人在遥远的原野上轻轻地唱着。“红血管的孩子,血液也是烫的。蓝血管的孩子,骨头也是蓝的。我是蓝血管的孩子,浑身布满蓝色的刀锈。结了晶的,厚厚积雪中的世界。坚硬的湖面,冻僵了的雨。没有春天,连风也不会有。”什么时候才能再碰见他呢?她有点后悔了。可是,留在一个病人身边,早晚会让他厌恶的吧。她一个人走过深深的河谷和潺潺的溪流。粉红的花朵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荒凉的冰天雪地的景色。在高高的山原上,雪松的针叶缀满了苍苍冰花。走到北方的戈壁时,平原的积雪已十分耀眼了。第七天凌晨的时候,她走到了冰海的边缘。远处,几只鹰隼在海的尽头高高低低地飞翔着。一只小鱼从水中跳上浅滩,她略微惊讶地看着它。不是那种草原上的会飞的小鱼,只是有着暗淡的紫色闪光鳞片。像一则美丽但是哀凉的童话。北风呼呼地、呼呼地吹呀、吹呀……暴风雪就要来了。这奇异的生命在干涸的沙砾上略微扭动了一会儿,便只有嘴巴一开一合、颤颤巍巍地出气了。她定定地看着,没有试图救下它。就在那一瞬间,她的身体突然不能动弹了。蓝色的坚冰从脚下,从手肘,从全身包围而来,很快抵住了她的咽喉。大海的边上,白色的雪尘开始旋转着跳起狂暴的舞蹈来。“救命……冻住了……”她沙哑地说着,用尽力气地哭泣着。“谁来救救我呀……”无人回应,她的声音消散在沉重的雪国中。晶明的空气里,突然出现一束温暖的赤烈的光芒。那个比世界上所有的炉火加起来都要温暖的人,正在几十米外遥遥地看着她。跟上次见到他时不同的是,他似乎是整个被包裹在一团火焰之中了。“是你!不要走……”她已经说不成话了。但他转身就跑了。“停一停!停下来!”他逃走了。唉,果然会让人憎恶。那小小的一团火焰似的身影,越升越高,越来越远。哎哎……那个人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冰原上什么也没有了。而她已经要结成一个冰茧了。是眼睛花了吗?他真的来过吗?但是,太阳已经慢慢地出来了。风雪停住了。她感到自己的蓝血管格格地松动了,躯干苏醒过来。冻僵了的手臂和膝盖渐渐恢复了知觉,脖颈、手指、脚趾……一直到每根头发尖都活过来了。刚刚一能动弹,她就立刻地向东方,向他消失的地方奔跑了过去。跑呀,跑呀,似乎是要把整个世界都抛在身后一样……整个世界在她的眼前展开成一幅巨大的画卷,是她从未见过的、比魔法的世界还要生动的世界……每一根正在融化的冰柱都挂着一滴闪亮的露水,大地上缀满了宝石。暴风雪后的云层霍地裂开缝隙,阳光哗然涌出,一丝一缕垂直地洒向地面,宛如辉煌的竖琴琴弦。一抹湿润的彩虹在树梢绽放光彩。无数野草的藤蔓一下子伸出了碧绿的指尖,而浓密的玫瑰正在如烟似雾地盛开。远处,云的巨海静静地蒸腾着。她的心里亮堂堂的,明白此刻有无数歌谣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兴高采烈地飘荡,来自稚嫩的,年老的,男人,女人……是了,这就是他说的春天。这是一个惊喜的、奇迹的世界。而他已经不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是在满天云霞下面,失魂落魄地跑着。回身一望,西山上的太阳明煌煌地,像那个人的灵魂一样燃烧着。张近微